2020-04-02 11:50 作者:中华健康网 出处:互联网
| 进入隔离病房工作,对于精神科和心理医生来说,是不小的挑战。除了担心被传染,每时每刻都处在在压力之下,心理治疗需要的很多有效的手段,例如语言交流,表情和身体语言的观察,穿上防护服之后,都受到了限制。 在医生群体中,“李文亮”这个名字成为了触发这场疫情伤痛记忆的按钮。“只要一听到李文亮的名字,我就难受得不行。”一位在武汉一线支援的呼吸科医生告诉“医学界”。 出发前,医疗队接到的任务是——为服务在武汉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,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,同时兼顾到患者的心理健康。 多数医护人员需要忍受照顾患者、缺乏个人防护设备,以及迅速变化的医院规程,带来的焦虑情绪。他们还放弃了伴侣和孩子们的陪伴。这与疫情中,我们大多数人所面对的孤独完全不同。 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刊发的研究调查时间为1月29日到2月3日,当时,武汉疫情正处于爆发期。正如研究人员所分析的,“确诊和疑似病例的数量不断增加,工作量繁重,缺乏个人防护设备,媒体的广泛报道,缺乏有效药物,以及缺乏得到充分支持的感觉,都可能加重这些医护人员的精神负担。” “达到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诊断标准的,我们则会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,时间30到50分钟。我们也会教给医护一些自我调节的方式,像呼吸训练、肌肉放松、心理着陆技术等。”王振说。 关键词 >> 新冠肺炎,医护心理,PTSD 李文亮的微博评论区,就像一个“树洞”,给疫情中愤怒、彷徨、恐慌、悲伤的普通人一个倾诉的出口,也折射出疫情之下,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变化。疲惫的医护人员/图片来自界面新闻 关注 王振在也碰到过多个出现无奈甚至自责情绪的医生。“特别武汉当地的医生,他们看到了很多的患者,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抢救,但结果还是有人离世了;或者听到自己的同事、自己认识的人染病后抢救无效去世,这种心理打击还是非常大的。”
但是,王振介绍,因为医疗队覆盖的人群有限,总体而言,他在一线接诊的达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诊断标准的病例并不多。 来源:“医学界”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:《疫情之后,谁来关心一线医护心理健康?》 王振带着第一组5个人,驻扎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。“一开始我们认为进入重症病房和患者面对面的机会应该不多,但是实际上这样的需求还是挺多的。”王振告诉“医学界”,必要的时候,他要穿着三级防护装备,进入重症病房,和临床医生一起做联合会诊,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或者精神状态。
正如美国精神科医生Najma F. Hamdani所警告的,“下一场大流行可能就是心理健康”。 巴林特小组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医生培训方式,聚焦于医患关系的病例讨论,但在引入中国后,原本以“关注病人”为主体的巴林特小组活动,却成为中国医护人员的心理自救试验。医生护士们围圈而坐,一个人讲述,其他人则静静地倾听。王振介绍,在武汉一线,巴林特小组确实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心理干预方式。
澎湃号 > 医学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调查研究的时间和样本的来源,也揭露了这项研究存在的局限性。正如两项研究强调的,保护医护人员,是应对新冠病毒的公共卫生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需要立即实施特殊干预措施,以提高接触COVID-19的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。” |
 为什么你一想到上班头就疼,为什么待在办公室里你感觉很压抑?是工作太辛苦了吗,当然不是。下面教你几招让你喜欢上工作。…………[详细]
为什么你一想到上班头就疼,为什么待在办公室里你感觉很压抑?是工作太辛苦了吗,当然不是。下面教你几招让你喜欢上工作。…………[详细]  上班一族的12小时心理减压法 朝九晚五是很多上班族的生活,但是其实每天真正得到休息的时间是很少的。据统计,大多数的上班族...
上班一族的12小时心理减压法 朝九晚五是很多上班族的生活,但是其实每天真正得到休息的时间是很少的。据统计,大多数的上班族...  如何消除女性心理的“性恐惧” 新婚的欢乐主要来自性生活,年轻人对新婚的憧憬也有很多原因是出自对性接触的渴望。但是在这个问...
如何消除女性心理的“性恐惧” 新婚的欢乐主要来自性生活,年轻人对新婚的憧憬也有很多原因是出自对性接触的渴望。但是在这个问...  教你快乐工作的8个心理小秘诀 为什么你一想到上班头就疼,为什么待在办公室里你感觉很压抑?是工作太辛苦了吗,当然不是。下面...
教你快乐工作的8个心理小秘诀 为什么你一想到上班头就疼,为什么待在办公室里你感觉很压抑?是工作太辛苦了吗,当然不是。下面...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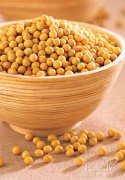 七大秘法 让你的内分泌乖乖听话 内分泌失调是许多人的烦恼。莫名其妙的发胖,面对爱人的不耐烦……这些生活中的隐患也许是因为你...
七大秘法 让你的内分泌乖乖听话 内分泌失调是许多人的烦恼。莫名其妙的发胖,面对爱人的不耐烦……这些生活中的隐患也许是因为你...